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在面向公众开展科普的过程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人们更多地会谈及媒介,而非单纯的媒体,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体平台化和平台媒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在于越来越多的科普工作者开始打造个人平台,绕过甚至是超越了传统的媒体,进而呈现出媒介化的态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内的媒介依然需要得到重视。
有学者认为,在众多传播科学理念的方式和机制中,大众媒体,尤其是具有娱乐导向的媒介通常最容易受诋毁和误解,虽然它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但同样的媒介渠道也有破坏或歪曲科学理念的危险,因为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往往不在意科学上的细节,比如电影、电视节目等为了夸张的效果而对科学进行的过度渲染,甚至存在夸大其词和断章取义的描述等等。与之相对的是,如今的科学研究已经开始从实验室走到了社交媒体之中,一方面科学研究结果越来越追求“可见性”,另一方面公众也越来越关注这些结果的“与己相关性”。
实际上,这是一种双向塑造的过程,也是一种需要处理彼此之间张力的过程。因为超越科技期刊的研究结果的广泛传播必然需要因应媒介传播的特征,也就是科学要理解公众,要理解让它得以传播的媒介,甚至也需要理解对科学进行传播的媒介技术,同时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也一定是基于个体的前置知识以及个人偏好的选择等。
因而,我们大抵上需要通过趣味或者说娱乐的手段来达到传播和教育的目的,而公众打开某个链接、某个视频或者选择走近影院观影的首要动机也脱离不开娱乐和消遣。当然,我们不能排斥这种娱乐和消遣,而是应该利用这种娱乐的选择而做一些文章,把科学内容通过某种娱乐的渠道或者媒介传播出去,只不过这需要结合与融合,也就是寓教(科学)于乐,比如早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有提及“推动科普作品创作工作,鼓励原创性优秀科普作品不断涌现。针对新时期公众需求和欣赏习惯的变化,结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成就和新趋势,大力倡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知识性和娱乐性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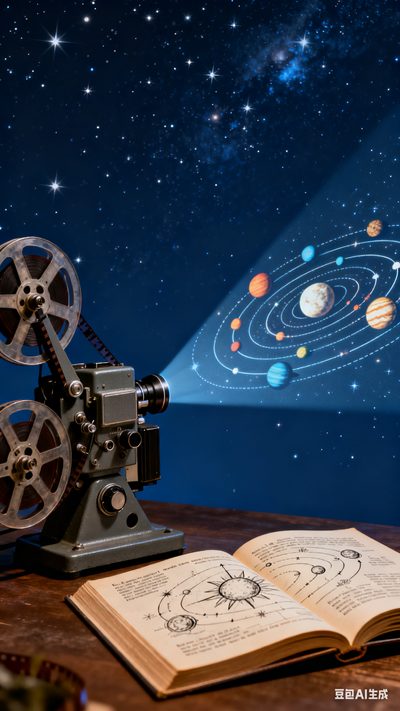
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就主张,电视等媒介的娱乐化将导致公共话语失去理性与深度,社会逐渐陷入“娱乐至死”的状态,因为在娱乐化的过程中人们习惯于被动接受信息,丧失批判性思考能力。我们当然要对这种情况有所警惕,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扭转这种过度娱乐的趋势,只不过在此书出版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我们似乎看到这种娱乐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任一个体都有意无意地被构筑了某种不愿意逃离的“信息茧房”,进而把思考的权利让给了别人。如果从科学与娱乐消遣的融合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趋势也给科普工作带来了相应的挑战,只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机遇,更好地推动科学的大众化。
要更好地开展科普工作,就必然需要在这种趋势中更多地嵌入科学内容,从而实现基于科学的娱乐消遣,或者说在娱乐消遣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实现了科普的功能,又或者说在娱乐消遣的长尾效应中将科学内容融入其中。从这个维度来说,电影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媒介。
2025年9月24日国家电影局、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国科协联合发起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专项行动,旨在通过推动电影与科普深度融合,发挥电影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上的优势,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11月21日,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2025年全国科普创作大会期间举办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分论坛,就如何做好台前幕后工作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实践,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当然,各专家的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科学类(也包括科幻类)影视的科普功能、价值、实现途径、二次开发以及科学顾问的角色发挥等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反观“跟着电影做科普”专项行动的具体举措,便可发现其中还牵涉更多的可能性。正如论坛嘉宾之一的林育智所言——让科学更好地走向公众,可能并不一定是通过科普的方式,而是通过文化或者娱乐消遣的方式。这其实也就是要从考虑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的维度来探讨如何更好地做好科普工作,推动科学与影视的融合,进而让科学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要理解科学的文化权威是如何建立和维持的,我们需要审视科学是如何在文化中被传播、解释和理解的。”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